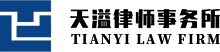
【论文摘要】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会见权做了较为详细的修改和完善。但实践中却出现了部分律师会见权被遗忘,部分被滥用的怪现象。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提升羁押机关管理水平,加强律师执业监督。
【关键词】律师会见 侦查阶段 执业监管
会见权是辩护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享有的基本诉讼权利,其设置目的是为了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开庭之前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有效沟通、充分做好庭审前的准备工作。目前,两大法系诸国家皆在相应的诉讼程序规则中规定了律师会见权。在我国,律师“会见难”曾经与“阅卷难”、“调查取证难”并称为刑事辩护律师执业的“老三难”。针对这一问题,2013年《刑事诉讼法》在修订之时专门对我国的律师会见权做出了修改和完善。时至今日,新《刑事诉讼法》已实施一年有余,备受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律师会见难的问题是否得到了有效改善,抑或产生了哪些新问题?这些问题对我国刑事辩护律师执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围绕上述问题,笔者对北京、河北等地多家看守所进行了实地调研,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律师会见权的发展进行了再思考
一、律师会见权之发展解读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第37条对律师会见权做出了明确规定,其主要呈现出下列发展特征:
第一,律师会见时间的提前化
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就是辩护权不断扩大的历史。律师介入刑事诉讼,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时间是两大法系诸国家衡量律师开展有效辩护的重要指标。这是因为律师展开辩护活动的第一步就是与犯罪嫌疑人会面,了解以嫌疑事实为主的具体情况。辩护人除了要提供给犯罪嫌疑人适当的法律参考意见以外,还要通过与犯罪嫌疑人的会面深入把握案件情况,确定辩护方针。在日本,宪法第34条就明确规定:“……如不立即赋予委托辩护人的权利,不得留置或拘禁任何人”。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7条第1款规定,被指控人在程序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委托辩护人为自己辩护。这一无限的获得辩护帮助的权利虽然在德国宪法中并未明确提及,但却被视为是法治国家宪法观念的组成部分。我国的律师会见权随着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其行使的时间也首次确定为“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被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标志着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从原来的审查起诉阶段大幅提前至侦查阶段。
第二,律师会见程序的自由化
囿于侦查机关对律师会见自由化的极大担忧,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是否应当受到侦查机关的限制是律师会见权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一直困扰立法者的问题之一。实践表明,一旦确立了会见自由原则的例外,那么这种限制律师会见的制度很容易被滥用。例如在日本早期,立法者曾确立了“一般性指定书制度”作为律师自由行使会见权的例外。然而实践中,按照这一制度,律师的会见权很容易被侵犯,甚至一度出现了原则与例外的颠倒。会见的次数、会见的时间往往因为指定书而受到限制,因而曾有日本学者对此提出了“会见买票制”的酷评。在我国,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明确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获得侦查机关的批准。其在实践中行使的效果与日本早年的“会见买票制”并无二致,甚至律师会见权被变相剥夺的案例也不鲜见。这实际上是侦查优先的观念在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人权法理论的发展,各国逐步认识到允许律师自由会见对于侦查机关而言,不仅可以防止其因独断而产生的失误,也可以提高对犯罪嫌疑人讯问的可信性。我国立法者在本次刑事诉讼法修订之时也明确规定,“律师持有效证件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即对于普通的刑事案件,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不再需要经过侦查机关的批准,而只要持相关证件,看守所就应当为其安排会见,且看守所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安排律师会见。这就有效避免了看守所人为拖延审核时间,阻碍律师正常会见的情形发生。表明我国的律师会见权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化。
第三,律师会见安排的科学化
律师会见程序的自由化是实现律师会见权第一层次的要求,即律师可以在无障碍的情况下在羁押场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而在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如何进行科学的安排,使律师能够在实施效果上真正达到律师会见的目的则是律师会见权第二层次的基本要求。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我国律师在行使会见权时曾遭遇到各种不合理的安排。例如绝大多数的律师反映其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侦查机关会派员到场监督,限制律师向犯罪嫌疑人详细了解案情;有的看守所甚至明确禁止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谈及案件情况,致使律师在会见时既无法了解案情也无法与犯罪嫌疑人直接商讨辩护策略。;由此导致律师会见的作用大打折扣,律师会见制度几近名存实亡。针对上述种种问题,本次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不被监听”。这一规定与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律师会见权的安排程序相一致,即将律师置于“可视而不可闻”的环境下与犯罪嫌疑人会见,这一安排既能够保障律师规范会见行为,确保犯罪嫌疑人在羁押机关可控范围内,同时又为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讨论案情,制定辩护方针提供了自由的空间。
第四,律师会见内容的扩大化
《刑事诉讼法》在第37条第三款中规定“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该条款虽然仅有短短的一句话,但首次明确了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除了可以向其提供法律咨询,了解案件情况,询问其是否需要代为申诉之外,还可以依法向其核实案件证据。这一规定无疑极大地扩大了律师行使会见权的内容。在刑事诉讼中,证据的收集和运用至关重要。由于我国之前不允许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调查核实案件证据材料,导致许多被告人在开庭之后才首次获知公诉方指控的相关证据,无形之中使得被告人一方质证的效果大打折扣。
二、律师会见权之实践反思
通过对律师会见权发展特征的解析,不难看出,我国现行律师会见权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相比,已经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笔者了解到,在新刑诉法实施的一年来,律师在侦查阶段提出会见申请的,看守所通常都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安排律师会见,并且为律师会见提供了较为便利的条件,例如北京和河北多家看守所先后推出了律师网上预约会见的举措,方便律师提前预定会见时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笔者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实践中针对律师会见权的行使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笔者将其概括为被遗忘的会见权与被滥用的会见权。
第一,特殊类型案件、特定诉讼阶段的律师会见权无法获得保障,这一部分会见权为立法者和执法者所“遗忘”。
首先,律师会见自由原则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已经初步确立起来,对于普通的刑事案件,律师要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已经无需再经过相关机关的批准。然而,对于特殊的刑事案件,律师的会见权通常还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也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规则的通行做法。例如在德国,对于涉嫌属于恐怖组织的犯罪嫌疑人而言,其与辩护律师会见要受到侦查机关的监控。这是德国律师自由会见原则的唯一正当限制。在韩国,对于恐怖组织犯罪、国家安全犯罪,律师会见的时间和次数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在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这是我国律师会见自由原则的例外规定。
然而,经过笔者调研发现,上述三种特定类型犯罪的律师会见权在实践中的行使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一方面,对于这三类案件,实践中能够获得侦查机关许可会见到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少之又少。绝大部分的辩护律师在代理这三类案件之后都无法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另一方面,现行立法仅是对该三类案件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作出了特别的限定,对于后续的其他诉讼阶段,辩护律师享有的会见权与普通刑事案件律师的会见权应当是相同的,都遵循律师会见的自由原则。然而,实践中,有相当部分的特殊案件,即使是到了审查起诉阶段,律师想要会见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然被告知必须获得侦查机关或检察机关的批准。
其次,对于普通类别的刑事案件,在一审判决后二审法院受理之前以及申诉期间和死刑复核期间,律师想要与案件的被告人或申诉人会见,依然困难重重。律师会见权作为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准则》中明确规定,“律师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均得以与其当事人不受妨碍地自由交流”。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关注律师侦查阶段会见权的落实与保障的同时,在实践中却出现了大量刑事案件,在一二审程序交替时期,律师无法会见到被告人的情形。此外,在案件申诉和死刑复核期间,律师无法会见到被告人的情况更为突出。
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律师会见权在特定案件中被忽视,在特定诉讼阶段被遗忘的情形,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其一为立法的模糊性。例如在三类特殊案件中,有一类为重大贿赂案件。这类案件在实践中数量较多,影响较广。但何为“重大”,却无明确界定。尤其在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涉嫌贪污贿赂的数额有可能是不断变化的,而数额的主动权则完全掌握在侦查机关手中。换言之,是否属于重大贿赂案件,某一贿赂案件是否要经过侦查机关批准才允许律师会见,完全是由侦查机关自行把握的,缺乏立法规范。其二为执法理念的偏执性。无论是对于公检法三机关抑或是看守所等羁押机关而言,由于受到打击犯罪理念的深远影响,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辩护律师有一种天然的对立情绪,总是偏执地认为辩护人充分行使了辩护权就会对打击犯罪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在法律出现漏洞或规范不完善的时候,通常自动地扮演了限制辩护权的诉讼角色。实践中各机关常以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为由,拒绝甚至禁止律师在某些诉讼阶段行使会见权就为明证。
第二,辩护律师在行使会见权时也存在违法违规行使,扰乱会见秩序的情形,这一部分会见权被律师所“滥用”。
根据笔者的调研,实践中常见的律师滥用会见权的情形主要包括充当“生活律师”进行会见和律师会见时故意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看守所纪律两种情形。所谓“充当生活律师进行会见”即有的律师以律师会见为主要业务,专门在看守所外,待犯罪嫌疑人亲属有会见需求时即与其临时签署委托辩护的法律文件,以辩护律师身份进入看守所申请会见犯罪嫌疑人。这些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目的不是为了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完善辩护策略,而仅为代替家属了解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内的生活状况或者替家属和犯罪嫌疑人之间传递各种信息。故而称之为“生活律师”。“生活律师”的这一行为,不仅违背了律师会见权设立的初衷,也严重地扰乱了看守所正常的会见秩序,导致部分坐席较少,会见条件有限的看守所出现了会见申请积压的状况。第二种滥用律师会见权的情形是律师利用会见时不被监听等条件,进行某些违法违规行为。在实践中较为突出的几种律师会见违法违规的情形有:律师在会见时私自将手机借给犯罪嫌疑人打电话,为犯罪嫌疑人传递纸条信息,协助犯罪嫌疑人亲属冒充律师助理参加会见以及较为严重的有律师利用会见时帮助犯罪嫌疑人串供或诱导犯罪嫌疑人翻供等行为。
客观而言,辩护律师滥用律师会见权的上述情形显然是立法者在《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初所无法预料的。任何权力,一旦缺乏监督和制约,必然会被滥用。从某种意义而言,权利的行使同样如此。探究律师滥用其会见权的原因,笔者认为,一方面由于律师的会见权骤然开放,我国的看守所尚未积累有效地对律师会见权进行监督和管理的相关经验,部分硬件设施建设也不完善。例如大部分的看守所尚未完成对律师会见室可视化的改造,导致看守所无法通过视频监控等方式对律师会见的全过程进行无声化监督。另一方面,律师协会等相关律师自治管理组织也缺乏规范律师会见的相关配套规则和惩戒措施,导致律师违规会见的违法成本较低,即使被羁押机关及时发现,通常也不会受到实质性的惩罚,对其执业前景难以产生负面影响。
三、律师会见权之制度完善
针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律师会见权“被遗忘”与“被滥用”的情形,笔者认为,应着重从下述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制定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律师会见权的立法规定。
首先,对于三类特殊案件,要列明在何种条件下侦查机关才可以不许可律师会见,将我国现行律师会见权调整为“会见自由的原则→作为例外可设定限制→从尊重会见权的角度对例外进行限制”的制度结构,防止侦查机关对会见权的例外限制做扩大的解释和应用。其次,明确律师会见权保障的范畴。规定对于普通的刑事案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律师均可持法律规定的相关证件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守所负有在任何诉讼阶段保障律师会见权顺利行使的义务。最后,增加保障律师会见权的相关救济制度。明确律师会见权的救济机关和救济程序,当律师的会见权受到不当限制时,可以自行向相关救济机关申请救济。
第二,改善羁押场所会见条件,提升羁押机关管理水平。
由于刑事诉讼法修订时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了侦查阶段,导致实践中律师会见的需求量剧增,大部分的看守所由于受到硬件设施的限制,还无法为律师会见提供完善的会见条件。以北京市朝阳区看守所为例,该看守所现有律师会见席位16个,全天可接待80名律师进行会见。但据统计,每天向朝阳看守所申请会见的律师数量则接近200名。这就导致大部分律师需要提早排队甚至连续排队几天才能会见到犯罪嫌疑人。较为极端的情形如律师需要向黄牛买号才能完成会见。这就对看守所的管理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增加会见坐席,延长会见时间等方式提高管理效率,保障律师会见权的通畅行使。在改善看守所硬件环境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律师会见权的规范管理。例如可为律师提供存储箱柜,要求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前将自身携带的电子通讯设备等妥善保存。通过网络信息管理和会见登记制度甄别“生活律师”,及时向相关律师管理机关通报律师违规会见情况等。
第三,加强律师管理与监督,加大律师违法违规惩戒力度。
对于律师滥用会见权,扰乱正常会见秩序的情况,笔者认为,一方面应当借助我国现有律师管理体制,加强对律师群体的管理和监督。引导律师正确看待法律所赋予的各项诉讼权利,树立依法执业的基本理念;另一方面,建立律师管理机关与羁押场所之间的动态联系机制,一旦出现了律师在看守所内违法违规会见的情形,特别是利用会见帮助犯罪嫌疑人串供和诱导犯罪嫌疑人毁灭伪造证据或协助犯罪嫌疑人亲属冒充律师助理进行会见的,一经查证属实,即予以惩戒,严重的可吊销律师执业资格。通过提高律师违法违规会见的执业风险来遏制律师会见权的滥用,促使律师行使会见权走上规范化的自治道路。
结 语
在刑事诉讼中,有的权利由于缺乏监督而被权利人肆意滥用,有的权利由于立法缺陷而使权利人不得不“望权利而兴叹”,像律师会见权一样,作为刑事辩护律师的基本权利,其中的一部分被律师滥用,而另一部分却被立法者和执法者遗忘的情形却并不多见,个中缘由发人深思。笔者认为,通过对我国律师会见权的反思与论证,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启示,即刑事诉讼立法需要考虑到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和各种特殊情况。同时,无论立法多么的完备,如果没有完善的配套措施,法律的执行都将大打折扣,甚至与立法的初衷背道而驰。因而,对于我国律师会见权的完善,要坚持将侦查机关、羁押机关和辩护律师群体都纳入到制度规范和保障的框架内,通过“权利——责任——救济”的制度设计结构来保障我国的律师会见权利健康有序的发展。
(本文发表于《河北学刊》2014年第5期)
版权所有 2009 北京市天溢律师事务所 备案序号: 京ICP备18027995号 技术支持:星诚视野
事务所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34号中关村科技发展大厦C座2405号(100081) 咨询热线:010-62122363